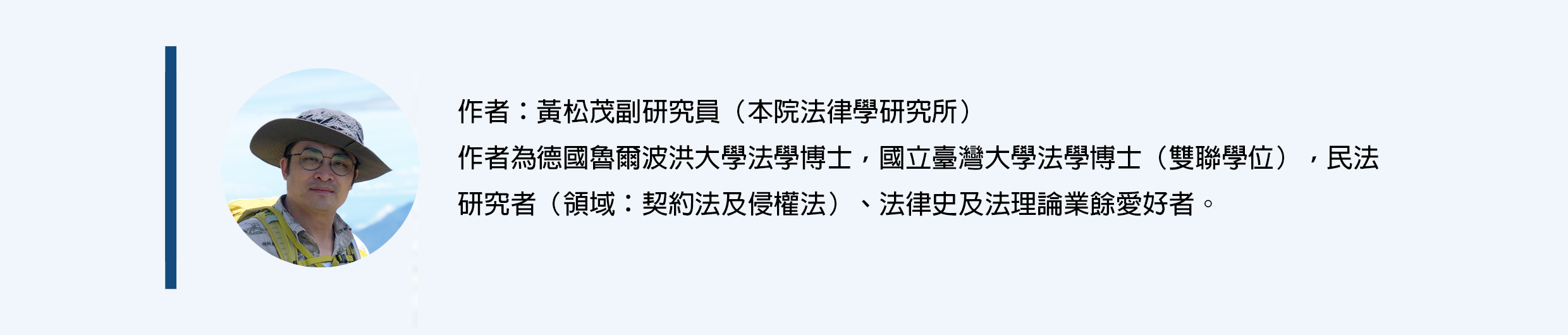發布時間: 2025-11-10
作者:黃松茂副研究員(本院法律學研究所)
作者為德國魯爾波洪大學法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博士(雙聯學位),民法研究者(領域:契約法及侵權法)、法律史及法理論業餘愛好者。
學術是一門良心事業,而良心指向人的精神(spirit, Geist)。在這個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圍繞著法的現象日漸大行其道、傳統意義下的法學(亦即法釋義學)貌似日薄西山的時代,筆者想要從傳統意義之法學角度,來回答筆者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質問的一個問題:「法律學研究所?法律有什麼好研究的?」。
法律與其他人類的文化成就一樣,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物,而是經年累月的成果。早在現代意義的國家出現以前,換言之早在John Austin以「主權者的命令」展開法概念的論述以前,已有數以萬計的法律心靈投入尋找法律、描述法律及建構法律的事業。他們的身分,可能是一名富裕的地主,只是把法的研究及傳授當成一門業餘興趣;也可能是羅馬皇帝身邊的法務大臣;也可能是修道院裡的僧侶,也可能是大學裡的教授;亦可能是政府官員。
無論如何,他們都或明或暗地察覺到,有一種規則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任何往來形式中,因著此規則之存在,個人得以保存及發展,共同生活得以維繫。無論如何,在這些專業程度由疏至親、由淺至深的法律心靈說出法之為何以前,已有可名之為「法之素材」(德語稱Rechtsstoff)的事物存在。法之素材,可能是官員的告示、皇帝的飭令或裁決、地方習慣的紀錄、行會裡的規章、教會的律令、現代國家頒佈的法律等。
法一旦以文字形式問世,即擁有某種程度自主性。猶如胎兒脫離母體,法律一旦被「說出來」,便享有自己的生命,頒布法律之人對於該法律呈現如何之形貌,自頒佈之日起便將控制之權柄交諸於他人,控制力逐漸喪失。國王死了,其頒佈的法律除非遭繼任者廢除,否則依然有其效力:「一代傳一代,人死法還在」。讀者如果知道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頒佈學說匯纂(拉丁文:Digesta)後曾明令「任何未收錄於學說匯纂的法學論述均不得參考」,以及1794年普魯士一般邦法典曾天真地要求法官必須嚴守文義、禁止類推適用,以及美國法哲學家Lon Fuller在《法律的道德性》一書中「雷克斯國王造法失敗」的寓言,將會對此處法之自主性的說明深感認同。
在各種形塑法之容貌的角色中—此處將進入本文的核心—法學家是筆者認為最重要的角色。此處的法學家,筆者採取一個廣泛的定義:任何參與法之形成的行動者,都是某種意義下的法學家,包含:法學教授、法官、律師及其他法律實務工作者。
19世紀德意志著名法學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將法學(Jurisprudenz,即本文所稱傳統意義下的法學)分為低與高兩種層次。低層次之法學,止步於以法律規則之形式呈現法律素材,而未能超脫於此之外,縱使諸法律規則具有某種嚴謹的體系亦然。高層次之法學,照錄耶林的用語,則是必須掌握法素材之「精髓」(Inbegriff von juristischen Existenzen),亦即將法素材視為「各種生物」(lebende Wesen)而掌握其精髓。
為達此一目的,耶林認為,我們必須在觀念上視其為形體(Körper),而觀察其「特徵、效力、形成及衰退之方式、所處之情境、所受之影響、幻化為何種型態、與其他法形體之關係」,而據此刻畫出受法之形體的個別性,並以合乎邏輯之方使其成為概念。耶林承認,此項任務兼具自然科學之研究及藝術創作之成分,因為,「法學家當下所要確定其本質的客體,正是由法學家自己所塑造出來」。換言之,在高層次的法學,法學家們的工作並不只是將法素材有秩序地擺放而已,而是從法素材中建構出法之形體。
何謂法之形體?在此用一個被後世譽為「法學上的發現」的法律原則來說明。若甲與乙締約,因甲對客體發生錯誤,致契約無效,有過失的甲是否應賠償乙因此所受之損害(例如締約費用)?甲不負契約責任,自屬當然,若侵權法也無相應之規定,乙便無法獲得任何救濟。民法大全中(拉丁文:Corpus iuris civilis,羅馬法素材之集合,是與耶林同處十九世紀之眾德國民法學者的研究對象)部分片段顯示,如果出賣人明知買賣的客體不存在,或者是禁止交易之物,卻仍與買受人成立買賣契約,出賣人仍須基於該買賣負責。
耶林透過檢視更多民法大全中之片段,得出一項結論:在契約與侵權責任之外,還存在一種責任,叫做「締約上過失」(拉丁文:culpa in contrahendo)。締約上過失此一責任型態目前在國際上被廣為接受,證據之一是歐盟羅馬公約第二規則(Rome II)第12條關於締約上過失責任準據法之規定。
部分法學研究者可能對低層次及高層次此一區分感到不安或甚至不滿,在此或可借用Lon Fuller倫理學上之分類:義務性道德(morality of duty)與期待性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依照Fuller的說明,義務性道德是最低標準,是社會生活得以維繫的基本要求,相反地,期待性道德則是人在最佳狀態下應採取的行為。Fuller在此極為生動地借用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之比喻:義務性道德「可比作語法規則」,期待性道德「好比是評論家為卓越而優雅地寫作所確立的標準」;「正如義務性道德諸規則規定了社會生活所必需的條件一樣,語法規則規定了維護語言作為交流工作的必要條件。正像期待性道德諸原則一樣,一流的寫作原則必定「是靈活、模糊和不確定的與其說他們為我們提供了達致完美境界之確定無誤的指引,還不如說它們只是描述了我們應當追求的這種完美境界」。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清楚的對應:「初級法學與高級法學」對應於「義務性道德與期待性道德」,從而開展出我們法學學術標準之內涵。初級法學,一如語法規則,其任務在特定(identify)並描述法律規則。此一任務的重要性,視其所處環境而定:在判例法國家會比在法典化國家高,在尚未被法律覆蓋之領域也會比已經由法律精細設計之領域高。雖然這並不表示,在初級法學並不會應用到同樣在高級法學所仰賴的創造力,但無論如何,在初級法學的層次,只要法學家成功描述法律規則,即屬達成任務。來到高級法學,筆者認為有幾個問題可以分別討論。
首先,追問法之從何而來,是高級法學層次的問題之一。對一條法律規定或法律制度,如果放棄認識其來源、背景、生成原因,那麼就像認識一個人只憑他當天的衣著一樣荒謬。舉例而言:一種似是而非卻常見的見解認為,關於法條文字可以透過直觀得出「文義」,惟文義有寬狹之別,故可再按照實際需要或透過評價加以修正(即所謂法學方法論上之術語「目的性擴張」或「目的性限縮」)云云。
不可否認,部分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文字相當接近自然語言,例如:刑法第10條第4項第1款規定,稱重傷者,包含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
「目」,指人的眼睛,並無太大爭議。然而,更多的法律規定使用的是規範語言,或者說,使用立法當時法學界所共同理解之語言。例如:民法第138條規定,時效中斷,以當事人、繼承人、受讓人之間為限,始有效力。如果不從規範觀點(進入規範的「境」),根本無從掌握該規定「始有效力」的意涵。最高法院 56 年度台上字第 1112號判決以該規定為據,認為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對債權人承認債務者,僅對該債務人發生中斷時效之效果,對其他債務人則否。然而,第138條規定並無隻字片語提到連帶債務人,為何該判決可以做出此一連結?
但如果我們瞭解到,我們的民法典帶有濃厚的多元繼受性質,而追溯這個規定的源頭,將我們的理解拉到立法者的層次(而不是停留在法條的說文解字),我們將意外地發現該規定與連帶債務的關聯,甚至與民法第747條亦有密切連結。
其次是法該往哪裡去的評價問題。縱使我國民法典不少規定繼受自德國,但難道這就代表,我們民法規定的解釋只能亦步亦趨地跟隨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又或者我們必須追逐最新、最進步的規定,例如:歐盟法中涉及民事的規定?這些外國的法律規定、實務見解或學說,難道不是在適應他們自己的需求嗎?我們臺灣自己的需求是什麼?我們自己面臨到的問題是什麼?
難道因為德國司法實務及學說一致認為,買賣瑕疵擔保的短期時效規定也應該適用於積極侵害債權,所以臺灣也應該仿效,讓民法第365條規定之時效也適用於不完全給付,使得以畢生積蓄購買房屋的買受人僅僅因為地震(德國一般而言沒有地震)發生在交屋後第六年,便無法針對耐震係數不合乎法令要求的房屋向建商請求損害賠償?是否僅因為歐盟各國以反歧視之名導入干涉契約自由之法令,我們臺灣便該不顧社會現實上未必存在嚴重種族歧視之現象卻貿然仿效,使得作為我國經濟主力的中小企業主隨時處在受罰的恐懼中?
其三是超越與建立臺灣法的主體性論述。從上述第二階段之評價已經可以發現,繼受而來之外國法律以及因襲成規繼受而來之外國法釋義學,有時無法與臺灣現實情況及正義需求相配合。事實上,在漸次民主化之後,臺灣逐步實現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並在此基礎上以越來越綿密之立法充實法秩序之內涵。臺灣的法學家應從此逐漸充實的法秩序內涵中尋找具有共識性的價值理念,並且在著眼於臺灣政治及經濟發展歷程之前提下,建立臺灣法的主體性論述,且以此為進行個別法律解釋及法律適用之基礎。在此建構主體性論述之過程中,必須強化臺灣法學長久以來欠缺之批判性。
最後值得附上一言的是:誰是承載上面所說這份法學精神的人?答案是:它或許可以從一個人身上看到,但更可能體現在幾個世代的法學家接續不斷的努力。所需要的,是接受這份精神,並在從初級法學提升至高級法學的方向上奮鬥。
參考文獻
Rudolf von Jhering, Unsere Aufgabe, Jahrbücher für die Dogmatik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und deutschen Privatrechts, 1, 1857, S. 1, 8-16.
Lon Fuller著,鄭戈譯,顏厥安審閱,陳郁雯、王志弘校訂,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2014年5月二版一刷,五南,頁32-37,65-73,。
顏厥安,法與實踐理性,2003年初版三刷,允晨,頁411-412:「台灣的法文化在政治解嚴後,反倒遭到了空前的挑戰,而且相當程度還是由法律人自行造成。由此亦可見到長年抄襲(這其實談不上繼受)外國之法條與與法學,而忽略法文化中之法律史、法理學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等層面,所形成的嚴重後果。缺乏了這種深層的共識理念,則任何浮面的法學理論都可用來精巧地為各種權利利益服務。畢竟法釋義學也只是價值信念與觀點的法制度性表達」
顏厥安,在這些神聖殿堂內,中研院法學期刊,第33期,2023年9月,頁237,259-260:「因此在『本土出發論、『本土不足論』之外,我倒是覺得可能還需要某種『批判不足論』來持續檢視我們觀察各種法事實的『認識框架』,這也包括批判檢視各種西方法體制與學說。」;262:「我則認為,法學思考可以更側重『類型觀察法』,也就是嘗試思考分析,既有體制與理論是依據如何的原理/原則,把社會現象『類型化』為不同法律概念範疇,並探索這些類型彼此的『流動性』以及可能可以如何重構這些類型。如前所述,這是一種對『認識框架』的認識論批判分析,這個分析也必然包含著對『知識』的歷史與社會條件的分析…」
顏厥安,欲哭欲笑據在伊—一個深綠學者不贊成大罷免的反思,2025年7月25日風傳媒投書(https://www.storm.mg/article/11055255)
先講一個見解:我「不贊成」這次的大罷免,主要的憲法學理由之一是:這整個「罷免權」的行使,已經有點類似德國基本法第十八條所稱的「基本權濫用」。該條文內容如下:......罷免權在台灣是否可能構成一種基本權濫用類型?不清楚,還需要更多討論。不過整個「發動與推動」大罷免的過程,倒是出現不少「疑似」言論自由濫用的案例。主要的要件連結點在於:無差別大罷免,是否構成一種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攻擊呢?王泰升,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2022年7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松茂,試論立體化之比較法方法-以時效中斷之相對效與絕對效為例,台灣法律人,第23期,2023年5月,頁44-58 。
黃松茂,台灣債法二度修正的十字路口,台灣法律人,第 2 期,2021年8月,頁21-39 。









 首頁
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