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青年政治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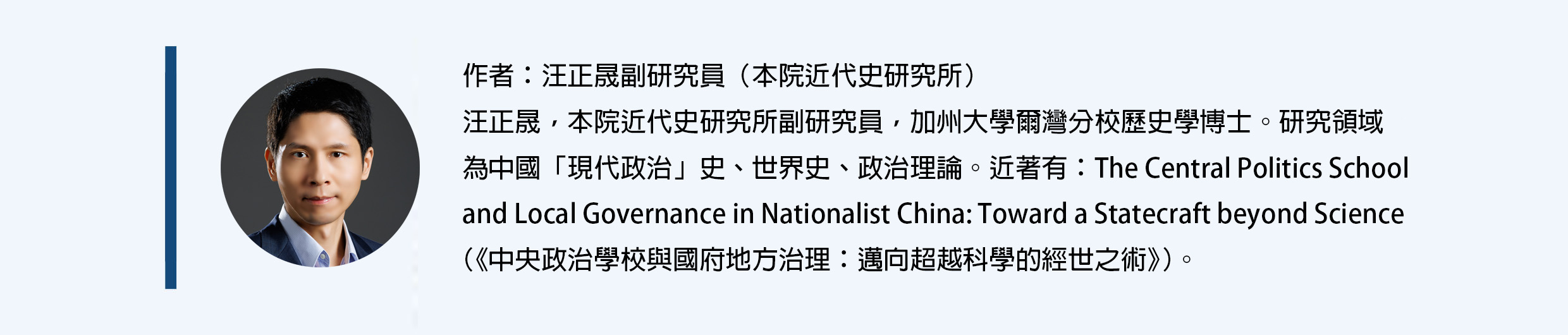
自從梁啟超(1873-1929)於1900年提出「少年強則國強」的命題,青年與政治遂結下了不解之緣。社會運動若要顯得名正言順,需要年輕面孔的參與,幾乎已成公眾默認的常識。世人似乎沒有意識到,青年成為政治中的要角,不僅在華人世界是二十世紀才有的現象,即使在西方,青年的誕生與政治崛起,也是到了十八世紀晚期才顯出端倪。
在此以前,不分西東,「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觀念根深蒂固。二十世紀初的維也納,雖是西方現代前衛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年輕男子仍有購買生鬚水以混充老成的實際需求。當時在政治上若以青年為認同或號召,自是有害無益。而年高德劭、通達世事的飽學之士向年輕學子講授傳統智慧,無疑是古典政治的常態。
隨著科學勃興,對普遍有效抽象原理的闡釋運用,雖需要一定天資,卻不必然仰仗特定文化中積累的閱歷地位。在古典秩序中,乳臭小兒即令有可能頓悟經世濟民的聖賢之道,也不具備號令推動的資格與德望。但在科學知識體系中,天才兒童以遠勝普通人的機敏,掌握運用強大自然力量的真知灼見,並非天方夜譚。吸收應用科學的先天認知能力,得到啟蒙專制君王的支持,由此成為質疑教會權威的重要理據。
在此脈絡中,青年從可與兒童混為一談的模糊概念,演化為具有先驗覺知能力的主體意識。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如德國哲學家尼采(1884-1900)在〈歷史學對於生活的利與弊〉中所揭示,上述科學想像已發展為一套宣稱青年先知先覺的世界觀,使青年成為「置身於生活之外」,「是歷史學和美學的知識庸人,是關於國家、教會和藝術的早熟新慧的饒舌者」。
也就是說,青年僅僅憑藉科學的抽象原理與推論方法,形成對傳統與生活間接片面的認識,掌握了區區理論或邏輯,即自信可以論斷國家社會政治風俗。簡而言之,科學催生了先知先覺的青年論述,使青年自信根據傳統之外的科學真理足以批判現狀,從而造成反建制的青年政治。
青年以反建制自命,十九世紀成了革命的年代。所謂前浪被一代代青年視為必須推翻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十年不到,登場未久的革命先進,又被下一代青年斥為阻礙時代進步的昏庸老朽。歐洲各國革命派固然以青年代表進步力量,要以青年的先知先覺來摧破舊制度,然而當權者亦不願自外於青年,無時不以爭取青年挫敗「反革命」為當務之急。百餘年間,革命與反革命派競相發展掌控青年的制度與手段,其中以中等教育體制的變革,最能反映青年政治及其技術日趨完善的歷史邏輯。
首先是以科學方法取代古典研讀,按照人文主義尊重個性、解放思想的理念,使學生熟悉以普遍有效的原理,進行抽象思辨的推論,將紛繁現實統攝於看似言之有據的理論之下,從而在報章與議會中樹立起足以挑戰當道的話語權。為滿足青年論政的需要,各種以小組討論為主要形式的口頭論理活動與場地,如辯論室、咖啡館,亦隨之大行其道。
二十世紀初,青年政治蔚然成風,甚至內化為市民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弔詭的是,革命形勢風起雲湧,此起彼伏,實際上,被革命推翻的政權卻寥寥可數。許多建制派改頭換面,化身為啟蒙導師,依舊大權在握,並未受青年衝擊而土崩瓦解。於是,一批親歷青年政治,如日中天卻又一事無成的青年,開始對自身的歷史侷限性,萌生最深刻的反思。
義大利共產黨領袖葛蘭西(1891-1937)在獄中反思革命失敗原因時恍然大悟,原來人文主義教育看似迎合青年一切想望,卻也使青年沉溺於抽象概念的修辭演繹,誤以為言之成理就勢所必至,因而喪失尊重經驗、實事求是、折衝樽俎的政治實踐能力,還不如古典教育有用,至少讓人知道變中有常,有所為有所不為。青年政治雖言論激烈,卻淪為當權者鞏固原有領導權的控制機制,實為求新求變者始料未及。
青年政治重視善於思辨的先天覺知,展示個人內心活動之聰明敏銳,成為提升地位與折服群眾必不可少之技藝。與此同時,當權者監控青年自我的需求與技術也應運而生。德國青年運動領袖班雅明(1892-1940)中年流亡巴黎之時方才醒悟,那位追求解放、尊重個性的政治家與人文教育家「宛如閃電那樣溫柔的眼光」,正在目光炯炯地「窺視學生們難以瞭解的內心」。青年自我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也領受到史無前例的凝視。隱藏內心真實想法的自由,既然是政治安全的威脅,自然受到政治控制的威脅。有關自我坦白與反省的精細技術,會發軔於大革命後政局動盪的法國,殆非偶然。
列寧(1870-1924)在1902年發表的〈怎麼辦〉,就是對這種困境的解答。深諳青年政治底蘊的列寧,為求克服青年「左派幼稚病」,反制建制派的監控,運用徹底規訓青年自我意識與小組討論,成為他實現政治行動自由的唯一妙法,這種犧牲個體自由以換取集體自由的先鋒派理論,深受班雅明啟發的法蘭克福學派給予了恰如其分的命名:「啟蒙的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西方青年政治演進之曲折,非啟蒙戰勝專制的正統敘事所能概括。當其隨西方全球霸權擴散至中國,箇中之奇詭,尤其無法以自由抗衡極權、進步衝決傳統的二元對立格局容納。事實上,魯迅(1881-1936)深刻體會到尼采的關切,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論〉中,以「先覺善鬥之士」一語,道破青年先天覺知與反建制的歷史性格。魯迅明知青年為西方文化中之偏至(激)現象,依然主張放棄面面俱到的穩健改革,以西方的偏鋒打響反建制的戰役。
這種激進思潮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成為學生信奉的主流論述。大量受西方新式教育的青年紛紛舉起科學的旗幟,響應胡適(1891-1962)提倡的尼采格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1919年前後,可以說是青年政治在中國正式登場的時刻,西方圍繞青年政治的攻防也在此際進入「極端的年代」。「創造適應於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國」遂成牽涉中外的國際政治博弈。
以其源自西方,中國青年政治無可避免地繼承了啟蒙造成的結構困境。崛起於五四時期的卓越青年領袖惲代英(1895-1931),透過直接閱讀英語文獻與中學任教的經驗,敏銳的體認到:五四之所以風潮一時即草草落幕,運動期間青年展現的政治幼稚難辭其咎。究其原因,正是西方新式教育「必欲養成一種歐美式的學生」。
惲代英自身所受的新式教育,同樣使青年習於「play idea」的抽象思辨,滿足於在雜誌與集會上放言高論,卻很少能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方案。更早於葛蘭西,惲代英開始掙脫將一切學科「哲學化」的課程典範,改從歷史文化中尋覓更貼近生活實相的教育模式。他放下拘執班雅明的「青年的語言」,亦即精思入微的批判武器,轉而以修己治人的踏實功夫,克制多言少行的政治無能。在五四稍後致胡適的信中,惲代英提出了莊子《齊物論》中狙公養狙朝三暮四之故智,試圖以隱蔽的政治「陰謀」操縱青年與群眾。
此種看似幽暗的意識,既反映青年蔑視倫常以自作聰明的先鋒習氣,卻又透露超越思辨,直奔組織實踐的跡象。深入地看惲代英「陰謀」的內容,可知他設想的陰謀家,實質上仍是有領袖精神,以身作則,苦民所苦的士大夫,只不過將古典教誨披上具有策略謀畫與操作效力色彩的外衣,使之能為喜好思辨科學的青年接受。
這套結合傳統治術與青年政治技術的思路,基本構成此後中國當權者應對青年政治的輪廓。以隱伏於群眾組織中的積極骨幹,用小組討論與自我坦白等技術掌控青年,使他們自覺獨立思考,自發服膺政令,實際上延續了西方二百年來青年政治的發展邏輯,可說具有普世意義,已非往昔中共的專利,而為今日各國以各式非政府培訓組織名義所採用,成為對內維持政治穩定、對外顛覆敵人的必要路徑。在全球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的時代,以青年敘事為號召,仍是政治運動源源不絕的深層邏輯。









 首頁
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