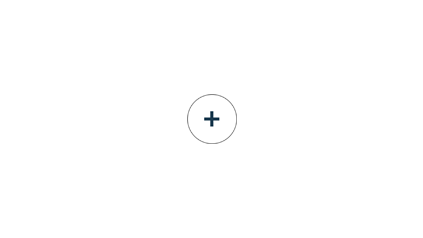發布時間: 2024-04-30
作者:陳兆勇副專案研發學者(本院社會學研究所)
共有地遭受的差別待遇
最早提出耕者有其田中共有地議題的應是經濟學者劉進慶。1992年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在臺灣出版中譯本,書中指出耕者有其田以徵收共有地為主。當時耕地按所有權形式分為個人有、(分別)共有、團體有三類分別做地籍歸戶,各有不同的徵收規定。如表1,徵收之前在總面積和出租面積中共有地分別佔50.5%、48.6%,均約半數,但在徵收面積中卻高達69.5%。出租共有地被徵收的比率高達81.8%,遠高於個人有地的28.2%。
出現這種結果是因為耕者有其田允許個人有地主可保留相當於中等水田三甲的耕地,而共有地主除老弱孤寡等共有以及配偶、血親兄弟姊妹因繼承而共有可比照個人有保留外,其餘一律徵收。會有這種差別待遇,劉進慶認為是因為共有地主「一般對於土地所有的財產觀念較淡薄」,對政策的抵抗態度較軟弱,軟土深掘,共有地就成了徵收的主要對象。
幾年後社會學者劉志偉進一步指出,共有地和個人有地在水田/旱田比例、自耕/出租比例,甚至區分為自耕部分和出租部分再計算的水田/旱田比例,都有著「極為顯著的相近性」(見表1;團體有地則有明顯差別)。此外共有持份也如同個人有地可以自由買賣。共有地和個人有地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只因所有權形式的不同,在耕者有其田竟有截然不同的命運。對此,劉志偉根據日後發放補償地價時共有人之間竟呈現出關係薄弱的現象,認為共有地主其實是一盤散沙,因此行政院敢於堅持共有地的徵收政策。
共有地的小地主屬性
進入21世紀後共有地又增加一項議題:一些研究者特別強調共有地的小地主屬性。2002年社會學者黃樹仁指出:若將共有地分割,個別共有地主「持份通常很小,遠低於農家平均耕地面積」,「不僅平均持份極小,且許多共有地的小地主是老弱、孤寡、殘廢等經濟弱者」。耕者有其田卻以徵收共有地為主,結果就是均富者少,劫貧濟貧者多。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若要將共有地辦理分割登記勢必需「大量人力與經費,耗費數年時間」,緩不濟急,國民黨政府(國府)於是選擇犧牲共有地主,以求儘速達成改革。
地政學者徐世榮則引用計算自地籍總歸戶統計結果的數據,推論被徵收的共有地「應該有絕大部分是屬於小土地所有權人」,這些共有小地主是耕者有其田政策下「命運最為悲慘的」一群。他認為當時政府堅持徵收共有出租耕地的原因有二:一是可能誤將共有地視為祭祀公業地,二是想將土地產權單一化。
官員和地主的共識(?)
這種共有地「小地主說」其來有自,在耕者有其田政策制訂期間官員和議員就一再闡述這類論點。辦理地籍總歸戶時農復會土地組長湯惠蓀就表示:共有地如要辦理持份歸戶「需要龐大的經費」,但「共有人數眾多,每人的持分,至為微小,分割計算,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因此農復會「多次研討」後決定不辦理持分歸戶。負責指導高屏試辦歸戶的熊鼎盛進一步說明:每筆共有地的共有人「少者二三人,多者至數十數百人」,若計算持分面積,「以甲為單位有的小至小數七八位以下」。據此,地政局長沈時可就曾答覆省議員:「共有土地總額雖多,但一經分開,即過於零細」。行政院在說明其草案時也表示:共有持份「極為畸零」,此種地主既不識其土地何在也不知耕種何物,「各共有人亦不重視此等土地之收益」,因此主張全部徵收以「消滅此種複雜錯綜之共有關係」。也就是即便一共有戶擁有的土地不小,但共有人眾多,分別計算後每人的持份就微小。就算當時出租(包括部分出租)耕地的共有戶確實也有很少數戶擁有耕地達幾十甲甚至上百甲(表2),但如果數十數百人共有,則分別計算持份的結果,這種大共有戶裡的共有人絕大多數也只是小地主而已。
顯然,擁有同等規模土地的共有戶和個人有戶(單一地主)相較,共有戶下的共有地主必定比個人有地主更偏向小地主。而當時地籍總歸戶的統計數據顯示,共有戶和個人有戶的土地規模分布差異並不大(表2),由此很容易推論當時共有地主比個人有地主更偏向小地主。而個人有地主就已經大部分是小地主了,可想見共有地主的土地普遍會更少,也就更加弱勢。
臨時省議會審議省府草案的過程中,省議員和各縣市議會的意見都沒有明言反駁過前述官員說法。事實上一些議員也以不同說法在強調共有地的小地主屬性,主要論點是:共有地多是兄弟繼承共有,或一人資力不足而與親友合資購買而共有。繼承共有的土地勢必較上一代更加零細,自身資力不足者能購買的持份面積也想必有限,兩者絕大部分都是較小的地主,經濟也偏弱勢。有議員就直接稱共有地的「小業主」,甚至有宣稱其「多係孤寡殘廢或不能自謀生活者」。省議會轉呈的一位市民陳情就凸顯這種困境:父逝後,母老弟幼,生活極端困苦,「雖略有土地,奈均共有」。因為報載政府十分重視小地主生活,他請求共有地也能和個人有地一樣可以保留。
官員為求改革成績會傾向多徵收土地,這損及地主利益。地方議會則會反映地主勢力的立場,致力維護地主利益。立場矛盾的雙方竟同樣強調共有地的小地主屬性,使「小地主說」更添說服力。而從「小地主說」和這些官員議員說詞相當契合一事來看,研究者對這些史料是相當熟悉的。
「完整的歸戶」揭露的實際狀況
「小地主說」並非沒有可疑之處。首先是共有人數。「少者二三人」和「多者數十數百人」之間差距甚大,而二三人共有恐怕難以導致持份「至為微小」。共有人數的常態究竟是個位數或數十數百對評估持份分布的零細程度相當關鍵。更重要的是,地籍總歸戶的作法有缺漏,不僅無法呈現地主實際擁有土地的狀況,還可能誤導研究者。
就上述兩點,當時苗栗縣地政人員王維伯和楊桓的〈臺灣省分別共有土地歸戶問題的商榷〉都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訊。該文指出,苗栗縣每筆共有地的共有人數「竟有達數十名以上者,平均亦在四人左右」。由於共有人數是正偏態分布(positively skewed),中位數會小於平均數,加上是數人頭,可知中位數是不超過4的整數,亦即至少半數的共有地是2至4人共有。
該文未提及數百名,應該是整個苗栗縣都沒三位數共有人的情況。可以推測,全臺共有地的共有人數應是以個位數為常態,數百人共有的情況極為罕見。官員模糊誇大的說詞有誤導共有持份零細程度的嫌疑。更嚴重是,研究者還往往疏忽了一種可能:單一共有戶的持份固然相較個人有地有更零細的趨勢,但同一共有人卻可能在不同共有戶下都有共有地,這是「戶」的資料裡看不出來的。而一戶的持份雖相對較細小,但幾戶的持份合計後就未必如此。
當時苗栗縣地政人員發現這種情況,認為必須將共有人在各戶下的土地歸戶才能知道其所有的共有地的總額,此即「持份歸戶」。他們還進一步指出這個持份總額還要和其個人有地合計,才是該所有權人所有土地的總和,這也就是「完整的歸戶」。簡單來說,地籍總歸戶是將共有人完全相同的共有地歸為一戶,有任何一人不同就歸為另一戶,故A-B-C三人共有的土地和A-B-C-D四人共有的、A-B-D三人共有的是分成三個共有戶來歸戶。因此要知道A究竟有多少共有地就必須將其在這三個共有戶中的土地再歸戶到其名下合計。而A還可能有自己名下的個人有土地,此時就要兩者合計才是其全部土地。
當年苗栗縣地政人員為此設計了一套辦法,在辦理地籍總歸戶期間也一併辦理該縣的持份歸戶,結果經費只增加約兩成,無須數年也不耗龐大經費。他們提出辦法,請各界垂教是否可行。但高層聽不到或聽不進,並未補辦持份歸戶,當時土地所有權的實際分布狀況也就無法得知。
幸運的是,黃大洲在1978年的研究提供了300位地主樣本的數據,讓我們可略推梗概。該調查先詢問地主改革前有多少土地(等於完整歸戶的面積),再問其中有多少是共有的(等於持份歸戶),將兩者相減就可得到其個人有地。改革前300位地主擁有個人有地和共有地的規模整理如表3,其分布狀況繪製如圖1。首先,從圖1不難看出共有地的分布和個人有地的分布相當接近。事實上如果做兩種土地分布的同質性檢定(一種卡方檢定),在0.05的顯著水準下可以推論兩者母體的分布是相近的。這意味著共有地並不比個人有地明顯更偏向小地主所有,共有地的「小地主說」恐難成立。
其次, 300位地主中208位有個人地,201位有共有地。可算出兼有個人有地和共有地者109人,僅有個人有地者99人,僅有共有地者92人,約各佔1/3。個人有地主中有52.4%兼有共有地,共有地主中有54.2%兼有個人有地。亦即這兩種地主身份約有一半是重疊的。
結語
認清上述現象會帶來一些新的看法。過往土地改革研究常有意無意預設共有地主和個人有地主是分開的兩群人,有各自的利益,而共有地主是其中更弱勢的一群。
根據這種預設又對共有地主∕個人有地主提出各種差別想像:一邊不關心自己的土地利益∕另一邊關心,一邊在地方議會沒有勢力代言∕另一邊有,諸如此類等等。但其實兩種地主擁地規模相差無幾,且身份高度重疊,利益相當程度交織在一起。共有地徵收政策並非只損害到共有地主的利益,約有半數的個人有地主也會受到影響。地主勢力豈會只爭取在個人有地上的利益,而不關心共有地上的利益?
如此再來回顧前述官員議員的說詞,就會有新的體會。官員其實是在為錯誤決策做辯護,不惜以偏蓋全、誇大不實。議員在提出各種保留共有地的主張時,並非只是要保護一般的共有地小地主的生計,也是在保護地主勢力自身的利益。最終省議會以本省耕地「間有兄弟數人,因繼承祖業為共有,如予以征收,恐生活發生問題」為由,提出刪除徵收共有出租耕地條款的修正案,就是在把維護地主勢力自身利益包裝在為弱勢發聲的正義言詞裡,試圖夾帶過關。整個談判過程雙方可謂爾虞我詐。官員當然一眼就能看穿議員們的話術。最終立法院通過的條例中只增列老弱孤寡和因繼承而共有兩例外條款,其餘共有出租耕地仍一律徵收,地主勢力終究徒勞無功。
參考資料
- 劉進慶(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臺北市:人間出版社。
-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編(1953)臺灣省地籍總歸戶統計。臺北市: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 湯惠蓀(1954)臺灣之土地改革。臺北市: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 劉志偉(1998)戰後台灣土地關係轉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9-53。新竹市: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樹仁(2002)臺灣農村土地改革再省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7:195-248。
- 徐世榮(2010)悲慘的共有出租耕地業主——台灣的土地改革。見謝國興主編,改革與改造:冷戰初期兩岸的糧食、土地與工商業變革,頁47-95。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湯惠蓀(1968[1951])地籍總歸戶的意義方法及其效用。見湯沈蕙英編,湯惠蓀先生言論集,頁145-153。臺北市:湯沈蕙英。
- 熊鼎盛(1992[1952])臺灣地籍總歸戶之檢討。見吳生賢編,臺灣光復初期土地改革實錄專集,頁676-687。臺北市:內政部。
-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1952)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專輯。臺北市: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
-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編(1952)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關係文書。臺北市: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 王維伯、楊桓(1952)臺灣省分別共有土地歸戶問題之商榷。土地改革2(8):11-12。
- 黃大洲(1985)臺灣農地改革對農村地主之影響。見李登輝編,臺灣農地改革對鄉村社會之貢獻:三民主義在臺灣的見證,頁70-113。臺中市:李登輝。











 首頁
首頁